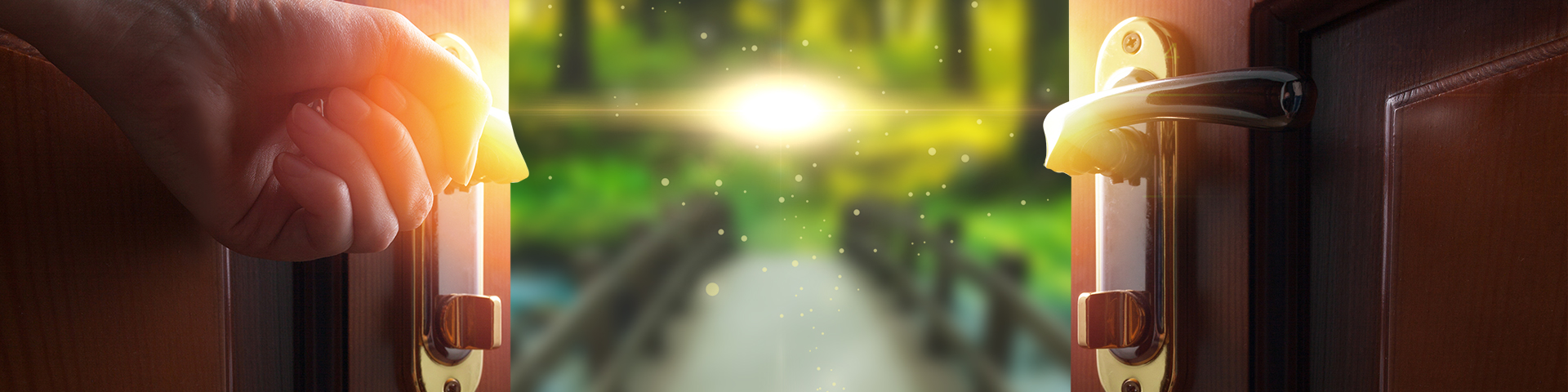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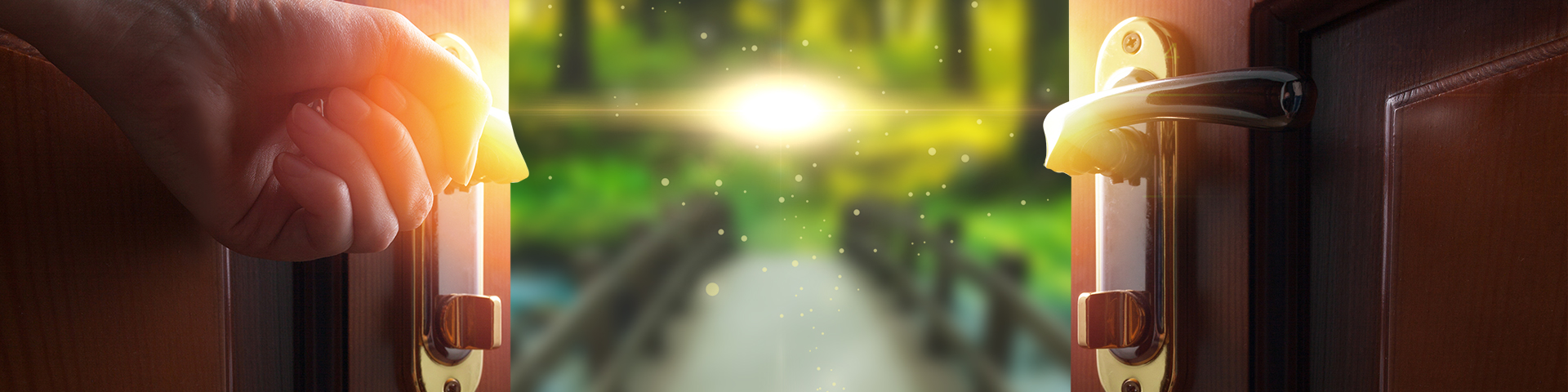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有的人為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無畏逆行”,但也有的人為了一己之私不惜借此天災進行犯罪行為。當前,全國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工作,需要依法、有序地展開,在此過程中刑事規制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和必要的保障。其中與我們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中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最為相關的當屬利用疫情實施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類的犯罪。
十七年前,我們國家也曾經歷過“非典”疫情,我們結合國家之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經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8號)的相關規定,將主要涉及防控疫情過程中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類犯罪犯罪行為以及與之相應罪名分為“醫”“食”“助”“行”四篇,依次分析總結。
(嚴厲打擊關系到人民群眾生活的哄抬物價、囤積居奇、趁火打劫等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違法、犯罪行為)
“一顆白菜50多元、一捆韭菜120多元,一個口罩40多元”。近日,全國各地陸續有群眾反映商家哄抬物價問題,這既刺激了群眾的敏感神經,也嚴重阻礙了當前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開展。
案例直擊:哄抬物價賣口罩遭罰 天津向價格違法行為亮劍(新華社天津2月1日)
一只進價12元的KN95口罩被抬高到128元銷售,被罰300萬元;10元/袋的口罩僅4分鐘后就改成15元/袋銷售,沒過幾天又漲到20元/袋,被罰50萬元……30日,天津市市場監管委公布了一批打擊價格違法行為典型案件,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不明碼標價等違法行為亮劍。
1月26日,天津市津南區市場監管局根據舉報對天津市旭潤惠民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柳盛道分公司進行檢查。當事人以12元/只購進KN95口罩抬高至128元/只銷售;以進價15.2元/盒購進片仔癀防霧霾口罩(成人1只裝)抬高至58元-78元/盒銷售。27日,津南區市場監管局將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送達當事人,擬處以300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并將當事人哄抬價格涉嫌經濟犯罪有關線索移送公安部門。1月27日,南開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依職權對天津市廣匯豐大藥房有限公司進行檢查。經查,當事人于21日以10元/袋價格銷售口罩,僅過4分鐘后以15元/袋銷售同一批口罩,26日又漲到20元/袋,連續多次推高價格。29日,南開區市場監管局將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送達當事人,擬作出警告、罰款50萬元的行政處罰。
天津市濱海新區濱瑞大藥房有限公司也存在哄抬物價行為,當事人以進價3倍左右的價格銷售各類口罩。1月28日,濱海新區市場監管局對當事人予以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處理。
經查,還有包括天津市隆興大藥房有限公司、天津市旭潤惠民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等28家經營者在銷售口罩、消毒液等防護用品的經營活動中,存在不明碼標價的違法行為,28家企業名單已予以公開曝光。
1、認定本罪的總體思路:違反國家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有關市場經營、價格管理等規定,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照刑法第225條第4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但該罪的入罪應充分考慮市場經濟背景下,因供需關系導致的價格浮動。對此類犯罪的定罪要逐案研究,一案一定,不枉不縱。不能輕易把屬于市場行為的價格調整視為非法經營,也不能縱容個別奸商破壞當前防災大局。
2、《疫情解釋》中“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違法所得和非法經營數額具有不同的范圍和計算方法。非法所得范圍較窄,僅包括行為人所獲得的純利潤。非法經營數額范圍較寬,不限于利潤,而是包括涉案產品的全部價值或者行為人的全部收入。最高院對此也給出了明確的答復,在《最高院關于非法經營罪中“違法所得”認定問題的研究意見》(下稱《研究意見》)中,最高院認為“如將“違法所得數額”混同于“非法經營數額”,勢必會引發認識混亂,并影響對相關案件的正確處理。”關于非法經營罪中“違法所得數額”的認定,我國司法、行政機關主張“獲利說”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刑事案件如何認定“違法所得數額”的批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上述《研究意見》都有相應的規定。《研究意見》認為,非法經營罪中的“違法所得”應是指獲利數額,即以行為人違法生產、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所獲得的全部收入(即非法經營數額),扣除其直接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的合理支出部分后剩余的數額。關于非法經營罪中“非法經營數額”的概念,我國法律并沒有統一的規定。立法機關采用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涉嫌非法經營罪的不同情況作出具體認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本解釋所稱“經營數額”,是指以非法出版物的定價數額乘以行為人經營的非法出版物數量所得的數額。”
3、《疫情解釋》中“嚴重情節”的理解:盡管《刑法》規定了“情節嚴重”作為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但沒有規定“情節嚴重”的具體內涵與外延。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在認定“情節嚴重”時均是參照司法解釋所設立的認定標準,而司法解釋通常是唯數額論或者以數額為基礎的綜合標準。在《疫情解釋》第六條中將“數額較大”與“其他嚴重情節”作為構成本罪的并列條件,因此對于本條中“嚴重情節”的理解應當排除數額因素。考察本罪的立法意圖,其設置是為了懲處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因此,是否達到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就是“情節嚴重”的一個重要參考標準。這樣理解,也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對于“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理解,目前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案例97號《王力軍非法經營再審改判無罪案》中的認定為依據:(1)對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適用,應當根據相關行為是否具有與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前三項規定的非法經營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進行判斷。(2)判斷違反行政管理有關規定的經營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應當考慮該經營行為是否屬于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對于雖然違反行政管理有關規定,但尚未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經營行為,不應當認定為非法經營罪。

@2020 版權所有:行通律所
津ICP備 11005639號
公安備案 12010402000900
技術支持:![]() onnuoIAD
onnuoIAD
電話咨詢
微信咨詢